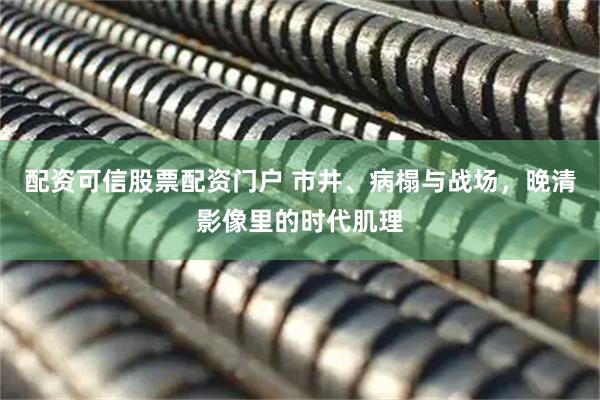
镜头扫过晚清的街巷乡野、宫墙之外,定格下一幅多元交织的时代浮世绘:广州花地的花市上配资可信股票配资门户,岭南繁花与瓦顶民居相映,市井烟火气蒸腾;乡村土坡的竹林旁,杂耍艺人的绝技引来村民围观,背后是底层谋生的辛酸;青楼的牌桌前,脂粉与牌声交织,既有社交场的暧昧,也有猎奇摆拍的大胆
清末,广州,花地(今芳村花地)的传统花市场,照片中密集摆放着成排的盆栽花卉(多为岭南常见的观赏花种),周围行人穿梭、驻足,后面是带有瓦顶、院落结构的岭南风格建筑。
广州花地自明清起就是著名的花卉种植与交易聚集地,到清末民初已形成颇具规模的花市,这里既是花卉产销的商贸场所,也是市民休闲逛游、选购花草的生活空间。
展开剩余84%照片中的是晚清乡村的杂耍表演,他们用桌椅搭起简易表演平台,一位成年杂耍艺人以双脚托举着孩子完成倒立动作,周围聚集着围观的村民,场地是带竹林的乡间土坡。
在娱乐匮乏的晚清乡村,杂耍班子走村串户表演是常见的消遣形式,“脚托倒立”这类平衡类技艺是传统杂耍的典型项目——它既考验艺人的力量与平衡能力,也是底层艺人维持生计的谋生手段。
这张照片是晚清时期一位身患严重肿瘤的普通民众肖像,画面里的患者骨瘦如柴,胳膊上的巨大肿瘤让他无法正常穿好衣物,只能半敞着破旧的衣衫,神情低落憔悴,尽显病痛折磨下的绝望。
在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晚清,普通百姓既无现代医学的诊断治疗条件,也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求医,这类疑难病症只能任由病情恶化。
晚清,青楼内两男两女围坐桌前打麻将,陪侍的青楼女子与恩客同局竞技,另有两人在旁围观;面对镜头的年轻女子妆容整洁、服饰得体,是晚清青楼女性的典型装扮风格。
在晚清社会,青楼不仅是风月场所,也是兼具娱乐、社交功能的空间——“女子陪客打牌”是青楼常见的经营项目之一,既满足了恩客的休闲需求,也体现了这类场所的社交属性。
1905年,北京,青楼女子与恩客合影,照片中女子梳着旗头、佩戴饰品、身着肚兜,男子赤裸上身,二人以搂抱的亲密姿态同框,这在晚清极度保守的社会风气里,是突破传统礼仪边界的“大胆摆拍”。这张照片应该是外国摄影师进入中国后,出于猎奇,刻意摆拍的场景。
这张照片是晚清农村团练,骑白马的成员持长械立于左侧,身旁几位团练身着短褂,肩上扛着长枪,右侧穿长衫、戴顶戴的乡绅,正是牵头组织团练的地方士绅,后面的石墙与山林,衬出这是乡村野外的集结场地。
晚清农村团练是地方乡绅主导的民间自卫武装,当时基层匪患频发、战乱波及乡村,乡绅便召集本地农民,配备长枪等简陋武器、统一简易标识,用以防范匪盗、维护本地治安;它并非正规军队,是乡村应对动荡的自发自保力量,也是晚清基层社会维持秩序的常见方式之一。
这张照片里的老妇人坐在雕花木椅上,身着袄裤,衣物质地整洁,手上还戴着戒指,身旁摆着小木凳,她的衣着与配饰都透着生活条件尚可的状态;身形矮小的她是侏儒,这样整洁精致的装扮,在当时残疾群体中并不常见。
晚清时期,残疾群体(包括侏儒)的生存普遍艰难:多数底层残疾者只能靠乞讨、或依赖亲友勉强接济过活。而这位老妇人能有安稳的坐具、整洁的衣着,大概率是依托相对优渥的家境,或是得到家族的妥善照料,是当时少数残疾者能拥有的较好生活境遇。
这张照片是宁郡卫安勇训练时的现场合影,草地之上,士兵们或蹲或站排成队列,手中持着统一的洋枪,能看出西法训练的队列雏形;但他们身上的传统服饰、头上的头巾,又带着晚清地方军队“中西混杂”的特质,身后的乡村民居衬出这是宁波本地的训练场地,旁侧的旗帜也点明了这是一支地方武装力量。
宁郡卫安勇组建于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是宁波作为通商口岸的特殊地方军队:初期有千余人,配备洋枪洋炮、采用西法训练配资可信股票配资门户,任务既包括保护在甬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也承担守城、维护治安等职责,算是洋务浪潮下地方尝试近代化武装的早期案例;但后期逐渐纪律涣散、战力衰退,最终在清朝灭亡时溃散。
发布于:四川省华林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配资可信股票配资门户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碳钢合金盘条第二次双反日落复审产业损害终裁
- 下一篇:没有了


